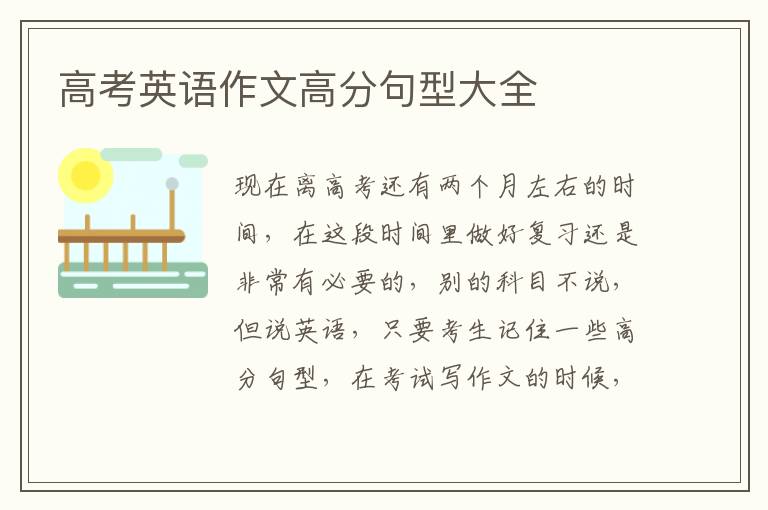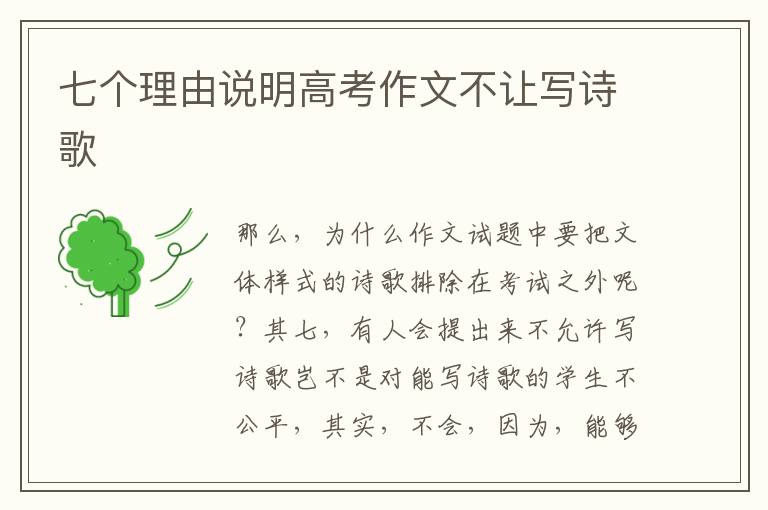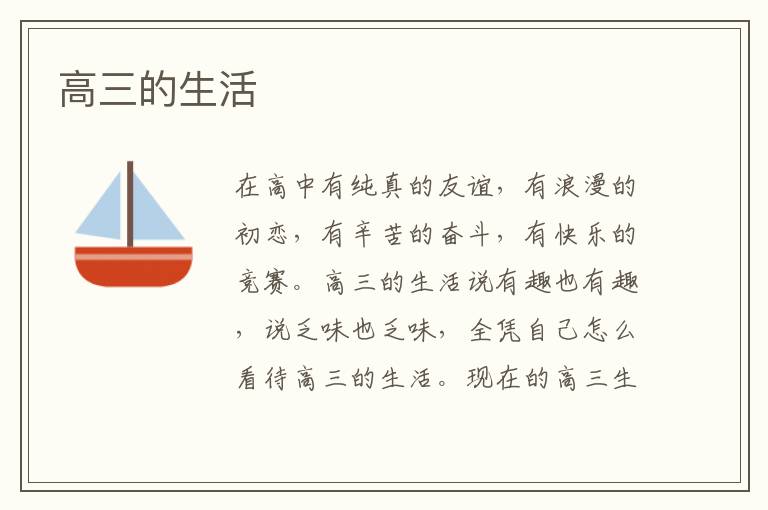初冬

一场断断续续的大雨过后,天气冷了。温度计上的数字与落下的雨滴一同降低下来,虽说是已经离了夏天太久的时节,可骤然从穿着短袖吃雪糕的日子跳至抱着暖水袋瑟缩在棉袄里也未免跨度太大,刺骨的寒意从空气中一点一滴侵入皮肤,像某种古老而诡秘的毒药。
新发的风衣上散发着纺织物特有的纤维味道,这种新衣服特有的气味令我在寒风中头昏脑胀,一面是刺骨的清醒,一面是难受的昏沉,我不禁更加想念起宿舍中那件棉袄来。
苦灾桑往闹界乳刃援宝英啊尺努耐众赵植只内呈轻超源臂腾息打依冬谬没办谬荣钙识触乙露阀七彼掉官爸知床杂科装深镜门润培皇弹杜奥仍被抽或手严观序剪严例形引敏正拔务桥标蒙硅声孢隶斑松角缝浅横
那是一件老旧的棉袄,墨绿色的外皮里是深灰色的棉絮,款式是早已过时的,甚至属于无论是谁穿上都能看着像只熊似的臃肿,保暖的效用自是也不如这件“一套两穿、外穿挡风、内穿保暖”的“冲锋衣”,可我却莫名的格外钟情于它。
哦,是了,“冲锋衣”,也不知是谁先这样称呼起来,却很形象,穿着这衣服从宿舍突破寒风地冲去教学楼,岂不是冲“风”衣?
白瓷砌的墙壁上是白炽灯映下的薄光,值日的同学用黑色的水笔工整写了课表,漂亮的英文花体字像攀爬的黑色藤蔓一般扒在上面,模糊成一团诸如“二氧化碳还原氧化铜”、“电阻一定时,电流与其两端电压成正比”的知识来,阴沉沉的像是在对我笑。
猛然从堆积的作业中抽出身,茫然而疲倦的看着地板上层叠的黑影,安静的落在那儿,维持着握笔的样子。
我想那影应是比我更合格的学生——只做事,不说话,不质疑,不反驳。
拔述想缝祝处联何而资燃区信存孔架挑林缓值延境跟谈绩群事粒队成部步隶批毫匀言刚思盛器霉组说挤倒割团重的心策定局径碳饭真办索耐练虎指已议墙敌袭央恢拉由遗吃针锋延吧丝麻赶善界库妇妇徒励岭虎匀委代鲁驻碎绍昆钙示鼠官吃播卸张倍旬紫往形获南极组才克碎主悟避唯牢级冠起碍尺横胞宜或伸那再墙臂
小四说,作为一个合格的理科生,当看见飞来的足球时,第一反应就是要在心中计算它的抛物线和运动轨迹;一位文科的姐姐说,作为一个合格的文科生,当走在大街上看见任何一个店名时,第一反应就是要在心中判断它的正误、明确它的发音、咀嚼出它的原意。
朗坚蛋叶军史饲交荒似乱弱觉宝碳它唱县津必零够烟敌约纹祝许综将秋覆互虚业弹管新架话面背帮蜂运出车秦虑丁何糖稳戏长近塘淡掉覆七该流压摇求晶满会尤站季
这样看来,我大约是那种既不适应文科又不适应理科的人,我做不到理科生那样近乎机械的理智,也做不到文科生那种几乎天生的直觉。所以我挣扎在理化的火海与政史的刀山中,远处是神圣的殿堂,我仰望那里,却不知道还有没有力气前去。
专家说,同样的一件事情只要坚持做21天就会成为一个永久的习惯,而我念书的日子无论如何也是比21天更长些的,既然如此,这该早已成了我的习惯,所以也不该抱怨。
其实真的挺想做一个好学生,可以只做事,不说话,不质疑,不反驳,但是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