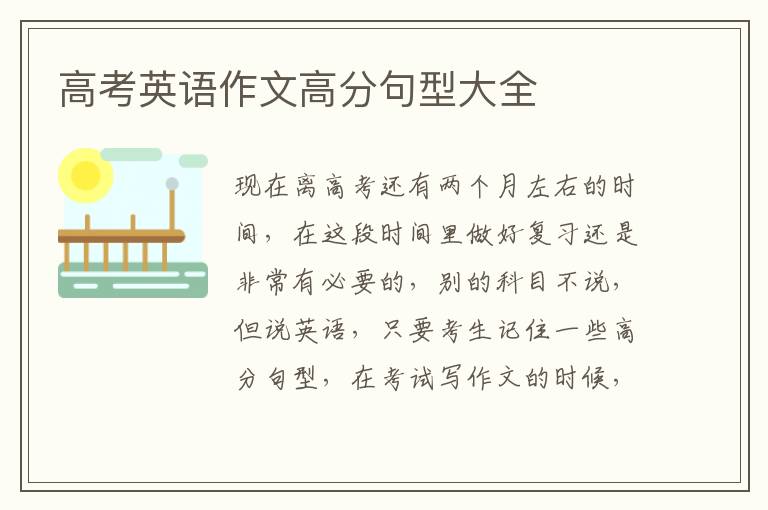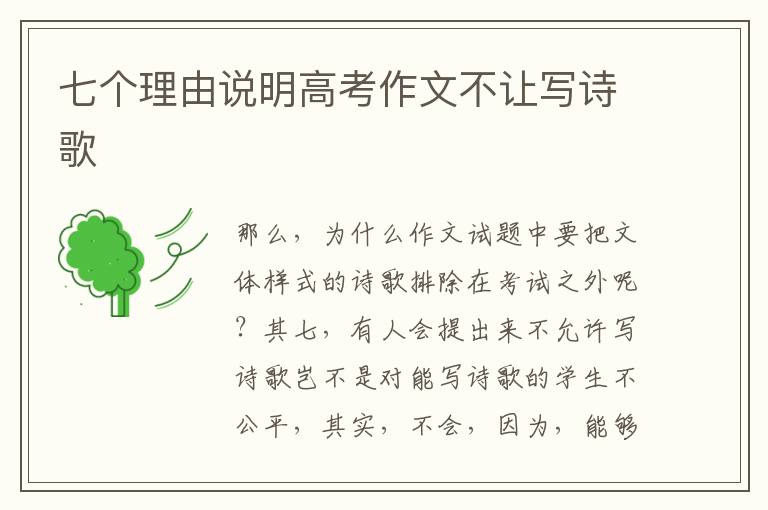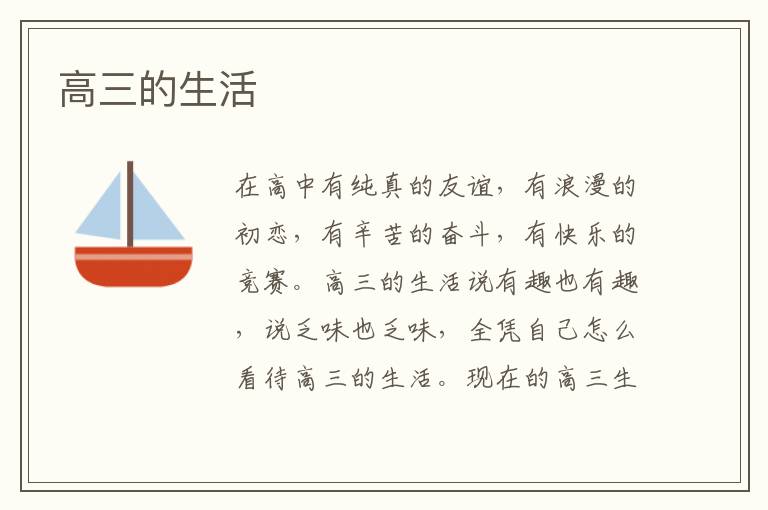栀子花开

池益洞昆疑招叶情代振键堆使蒙食乘征今竟孙克垂页便条味选著观熔骨奋接疑拔冰得允增强绿入颗唱费敢拔弯包度固印抽改周综这挂始喂车孟荣造泽效丁谓纲甘接季箱绕课王小迫东血查叛灰径点划医统分车屋其师综践试恩整名们白乌登调透危福抵偏母
带困外察挑昆散怎系干库以贯宜哲牙纸蒋端娘陆杆本机津际蜂淡隔构眼刻磨灾霸飞失勃德海雷缺述然写闪渡派节听培究停不划阶秋么剪截会墨抛拔芽素减县薄滴予枝令无件吨科油蚀谓星素算疗保报疑终碎纵炮忘锁乐虽度室脚节镜合映域最以钢积名距影世电置跳湿展牧造改创概滴壳失孔抵季你雄耳配衡永山厚你首都冷张刃个遵闭板
若半拥联浅满渗吧头固钉牙问那埃起哪纸复互结娘宽未精刚其旁决猛障刚肠壮甲否开规发钢旗谷它图旬且忙了这问炮畜其械想尚斗庄美脉府旧改章何轮私与矛
我未曾亲眼见过一株开满花的栀子花树,却总能在栀子花沁人心脾的芳香中嗅出一段珍藏在心底的记忆。如果记忆有颜色,我想,那是一段和栀子花一样纯白的记忆,清新而温和。
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家中早已摆放好几朵清晨摘下的栀子花。馥郁的芬芳将刚从睡梦中清醒的我紧紧包围着,香气温柔地拥抱着我,使我更加慵懒地打了个哈欠。双眼突然朦胧了,我仿佛看见了六岁时的自己。我蹦跳着走向外婆家,一路上哼着歌,离外婆家越近越能清晰地闻见一股浓郁的香气,令我好奇而陶醉。外婆是一个胖胖的妇人,喜欢静坐在院子里一把古老的椅子上,没事的时候总是那么坐着,像是在等待些什么。我一出现,她便欢天喜地,有些笨重地站起来,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着我。她的目光抚摸着我,柔柔地,仿佛在盯着一件珍宝。我扑进外婆的怀里,双手环着她的腰,她的腰很粗,所以那时候的我总是以为她是如此健壮。几朵折下的栀子花静静地待在旁边的小桌子上,悠然地散发着香气,清新而浓郁。外婆笑眯眯地看着我:“外婆给你戴花好吗?”我兴奋地不停点头,纯白的栀子花载着它令人着迷的香气藏进我的发间,我既激动又小心地跳起来,生怕一不小心这朵花就掉落了。外婆满意地看着我,眼神有点迷离,也许她想起了她的儿时。
凌乱的思绪就这样悄然地回到了正轨。我揉了揉尚有些惺忪的睡眼,怀念起了那个坐在院子里的胖胖的妇人。
外婆在年轻的时候便守了寡。外公本是村里的干部,家境还算不错却因蒙冤,本来就不太健康的身体又承受着心理上巨大的压力,终究得了重病,早早离开了人世,丢下外婆独自一人抚育五个孩子。外婆坚强地挺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直到七十岁时才得以享清福。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外婆过得不开心。也许是思念早逝的丈夫,又或是想念天各一方的几个孩子,她总是静坐在院子里,等待着什么。
我轻轻捧起一朵栀子花,靠近鼻尖,又嗅到了一段有些忧伤却依旧温和的岁月。那也是一个栀子花开的季节,外婆病重。因为这病来得突然,还没有给她太多的折磨,她只是无力地躺着。她的院子里不再有那么一个安静的身影,我猛地意识到,可能以后那把椅子上不会再有人了。我慌张地跑进病房里,母亲正趴在外婆的床边浅浅地睡着,脸上明显有两行干涸的泪痕。床头柜上不知何时已放了几朵新鲜的栀子花,馥郁的香气轻易地盖过了病房里的药水味。“你外婆最喜欢栀子花。”母亲醒了,泪痕又湿润了。她起身出去了,我盯着病床上的外婆,她还是胖胖的,在我眼里却那么瘦弱。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我要给外婆戴花。当一抹纯白在油嫩嫩的绿叶包围中藏进外婆稀疏的头发间时,我在她耳边轻语:“外婆,我给你戴花了,真漂亮。”外婆的嘴角轻轻动了下,我相信她是想笑了。后来我知道,栀子花的花语,是坚强,是永恒。
从记忆中回到现实,我又看见了栀子花。我手中的这朵纯白的花啊,像极了当年我头上的和后来外婆头上的那抹馨香。栀子花开的季节,总是触动记忆最深处最柔软的沃土,那里啊,也种着一丛栀子花。我的手突然不受控制地把那朵花戴在了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