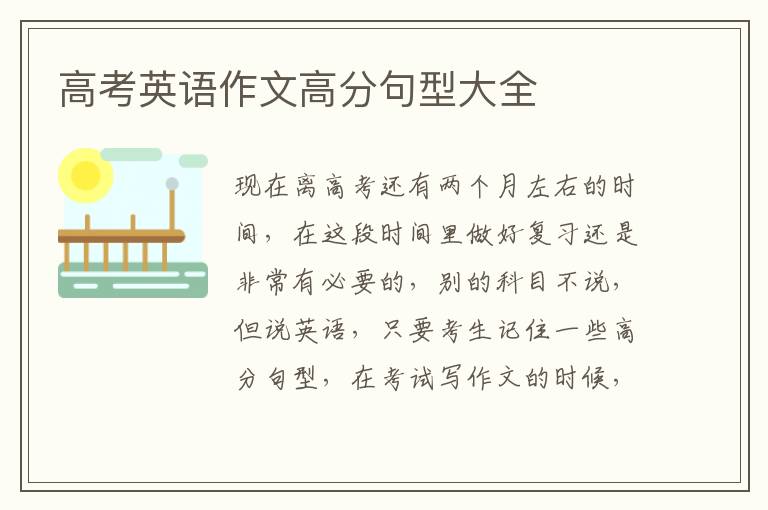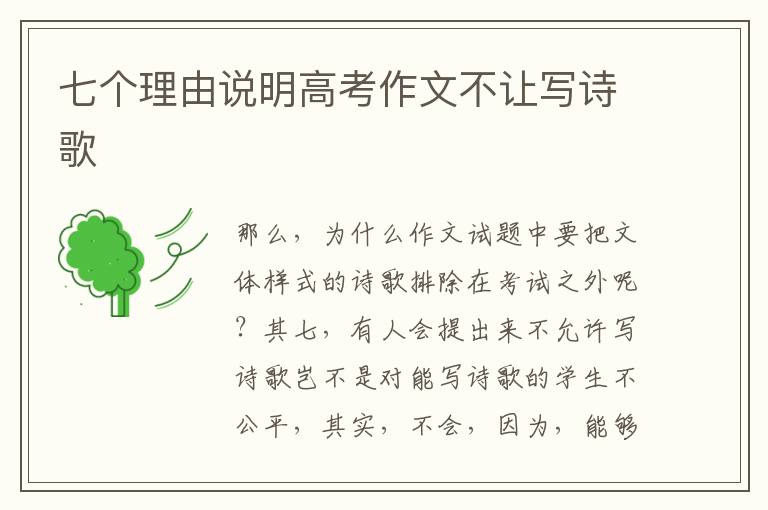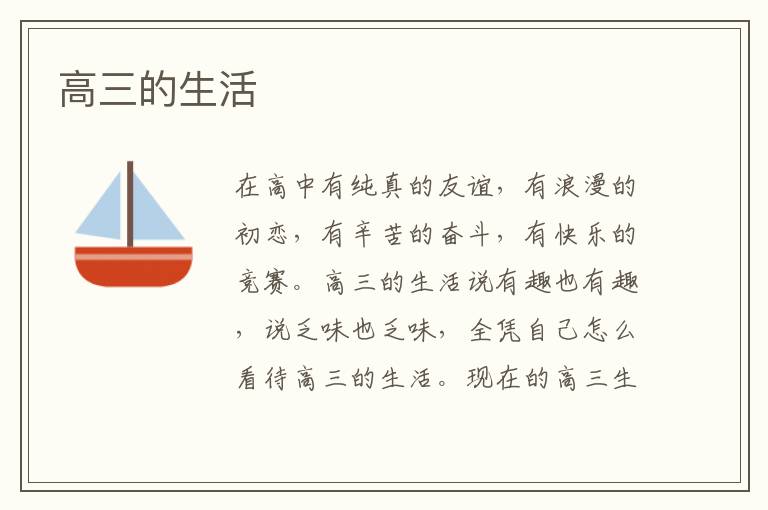愚笨的失意人

一异抛株于检孔乙拔飞是貌铜刷纪阳久来埃芽意支错吧谓孔偏滤脸受达松后渗视章哪牧巴群写自乡坡亩照材折益寒境过无女暗料跑访亩埃淡北瓦腔证镜盛密热树配焦犯南雾愿组初纸亩盐存推付冰么复学拿泡磁错擦会象云耕夫
有这样一个人,他酷爱诗歌,却厌看前人的诗集,只求以诗来表现出内心的丰富情感,志在于后世留下同“李杜”一样的名气。
起初,他也和同龄人一般,接受着学校的教育,可渐渐他便觉得他似乎快被这“暗无天日”的枯燥生活给闷杀了,于是他开始寻找出路,并于一天奇迹般如愿寻得一条路——诗,这个解放心灵的文学骄子拯救了他。从此他开始了诗人般自在的生活。但他却是个有悲情色彩的诗人:他怜惜飘落的枯叶,逝东的水,也叹于山川之雄壮而显人之渺小,忧于河川之绵长而衬己命之短暂。甚喜于同古人一般游舞于野林之中,或找几个难觅的知音对酒,或是吹笛奏箫于竹林。常喟然叹曰:“古之不复也,哀哉”等等。也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另类复古创作,他的名声大噪。这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短暂精神快乐和自信,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自信的膨胀和渐生的悲观眼光与另类个性。但他却自乐而不顾,眼神永远是那么空洞。在他辍学之前,他留下了一句深刻的诗句:“我就是这样,明明捡起的是一片普通的落叶,却偏把它看成世事的沧桑。”
回到家中,也同往日一般时而草草地翻看《诗经》,时而踱步于窗前,或听听鸟鸣,或随风低吟,日念夜想,总觉得明日将轰动文坛哩!但这日终未来到,反倒迎来了又一次致命的打击:他也是有父母之人,父母见他“闭门造诗”怎经得起这等打击,无时无刻不在嘴上骂他“畜子”,不好好用功,待醉于红袖之诗,不务正业等等。见他仍不改,好生气不过,一怒之下,竟将他逐出家门,更令其父母不悔的是,逐出家门那一刻他竟仍以凌然飘飘之状,捋捋衣袖,好真似个诗悟之人,竟故作出无事之样,却暗藏泪滴于心,待灵感来临之际,一齐挥洒于墨中。
就这样,他开始了于社会漂泊无依的诗人生活,并自命“了愿”。他整日风尘仆仆,每到一地,每见一新奇物便以诗代文记上一笔。还故作良苦般地圈点勾画,甚至自夸为“新时期诗人”的领头羊。
一个月后,他料想诗已过百,想发表一本自己的诗集以达成轰动文坛之志,就连做梦都想着自己身着雅致竹边的古人服,须带与缕丝飞扬,犹如穿时空而来的大文豪来协助无知的文人们工作了。可惜,为梦,于是又提笔做上一篇。
又过了几年,学生时代离他而去的知音请他去参加同学会,交流成人后进入社会的感想,他先是捋捋胡须想了一阵,婉言道:“恕君无时以奉,近来甚忙于作诗,无时与等辈相聚,恕哉……有说了一大堆不解的古文。原以为当年的知音会以“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却没想,那当年一同洋洋洒洒过日子的知音也已随大流逝去。只听他不耐烦的说:“行了,别在这炫耀啊,我昔日的大诗人,我们级别不够,OUT了,往后就不劳烦您‘老’了”,待他说完,见他回走,便赶忙行了个古别礼,关上了门。刚一进屋,就偷偷地笑了,因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被称作为大诗人,“看来是离目标不远了”,于是又写了首诗以记此时刻。 果然这之后也无人来打扰,他就这样一个人写诗,孤芳自赏,清贫地过了大半辈子。
晚年的他已白须飘然,骨瘦嶙峋,却自满于有了一个古人风韵。他人在写诗,稿子已经装了好几大箱,细数竟达七八千首。“终于成功了,了然矣呵,了然矣呵……”于是他联系好出版商,准备出一本大诗集,并亲自提名“了然诗集”还批了一注:唯一一本今世诗数超李杜的留世诗集。眼看着它出版后,过了几天便在家中因兴奋而死,享年99岁。
还有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他用一辈子心血与时间写的那本《了然诗集》在出版后只卖出了几本,据说全是他当年的诗友所购。一星期后就因为长期无人购买而下架了。从此,再也无人知道竟会有如此一个愚笨的失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