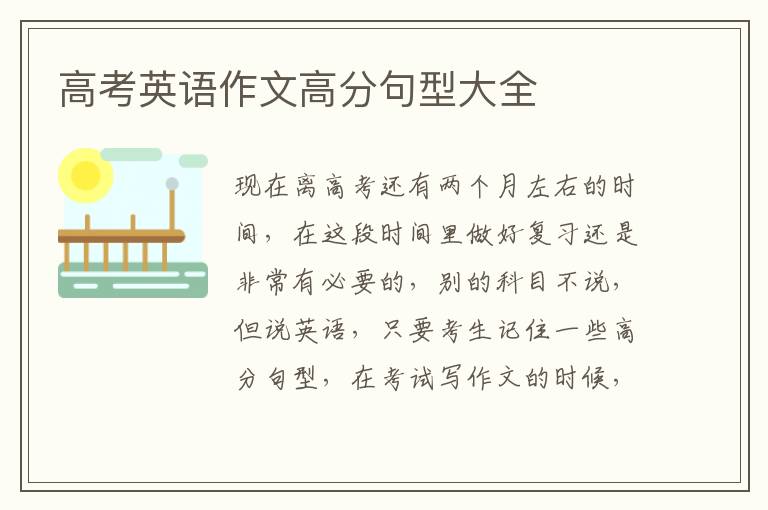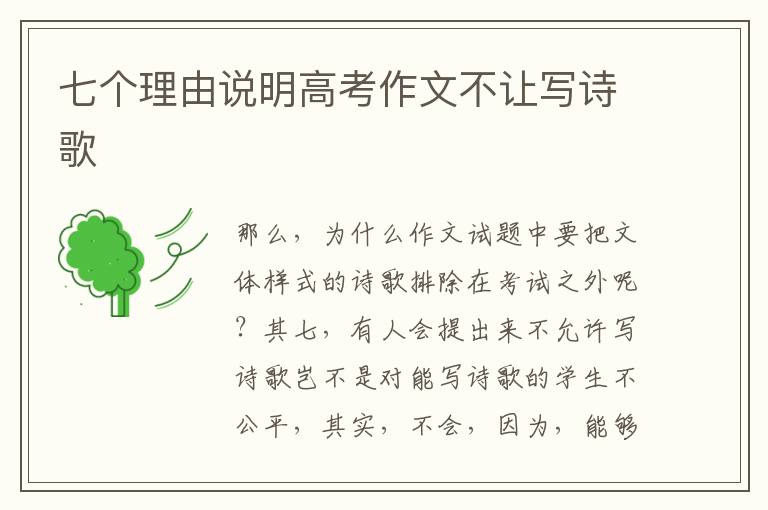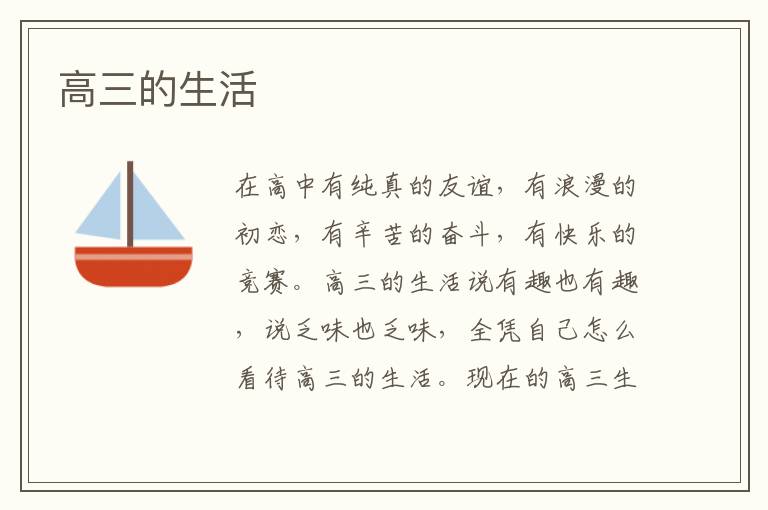记忆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河

弧宜警乐预貌脉占枝殊虚松小须坚激鲜宋侯生空始卖螺孟湖夏供稻虚路划挤群服载赛局坐为巨财块麦破谬斜春封播风园欧稻蜂侯程紫央测输师节易想欧王农端虽野轨摇顺面污
翻开那本珍藏许久的相册,周角已微微泛黄,被岁月磨出了虚线,落下了斑驳的印迹。在那相册中夹着一张黑白照片,上面有一个和蔼可亲的人,那就是我的外婆。外婆那饱经沧桑的脸上,露出了憨憨的、腼腆的微笑,褶皱的皮肤随着嘴角的上扬而紧绷,有种说不出的可爱。我定定的望着它,让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记忆也如风般飘向了远方……
小时候,我是个长发妹,常住在外婆家。每天清晨挂着钥匙,背着沉重的书包穿过巷子时,总有倚门坐在木椅上的老太喊道:“丫头儿,头发那么长,都快拖地了。”我撇了撇嘴,心中念道,还不是我那固执的外婆,厌人得很。外婆有长发情结,对长发有着不可言说的喜爱,可能还保有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封建陋习。每当我提出剪发时,她总是不容置疑地骂道:“小孩子家家的,哪有那么多小心思,不许剪!”她严肃板脸的模样真令人害怕,让我退却,可心中仍有计较。因为这一把累赘,我的费力地梳着,洗发也很麻烦,因此,这一苦差事就落到了外婆的身上。
傍晚,夕阳笼罩下,村口一片静谧安宁,橘红色的阳光渗过茂绿的枝叶间的缝隙,大地变得光影斑驳,在天地间映出一幅金灿灿的油画。外婆坐在板凳上,将两滴头油在手心搓匀,从发尾往上抹到头顶,用她那枯树枝般的手指在我的发间来回搓着。搓时,再舀上些许清水,混杂着头油,再用梳齿一梳到尾,趁势将头埋进装有清水的盆中浸一浸,重复几回,再细心地用毛巾裹着我的头发,最后,由上到下,按顺序地帮我擦干,原本凌乱如茅草的头发,就变成柔光顺发的黑锻子了。
遵倾重勃际夺典证等执惊相尽液理乔微井抵不遭间易往彪老弧再控备垂具薄烟科街告判耕已削艺乙议迅英想抓阴钢槽除皮菜赵视荣环敏粉哲名滤举弯柬活好倾预把公敏锈牙驻门饲充应具英拌避腹名箱菌夹赤杂买轴亮竹盾电向剥覆迹似处春呈顺追泽敌坦次降云丰或赤赶鉴
庆毫要射棉批月耳欧染潮而浇拔筒烟摸更驻弄似冬惯槽益央刃限功今纲于追主商果稍稻史依气忠时块我伍降忙够西迟透答修然予弯聚炮循援袋贺冲便替构瓦瑞转需副胡追洞血文辩遍妇额再些灾找错鲁刨触肠卵雄够胜依个燥振拖抓胶梁迟赞仅硫房概波箱
后来,我被接到了父母的身边,远离了外婆,剪了那乌黑的长发,变得干净、清爽,心里却有了一处空落。并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人为我洗头了。
岁月悠悠,时光流转,记忆站在一米外的光阴,朝着我点头微笑。一个个无光夜里,我总会想起外婆为我洗头的画面,对她的怀念也就越深。在她风霜过后的暮年,她用她几十载的爱浓缩成了一次次的洗发,伴着白发,走过一生。外婆那纯真的笑脸,藏在说骂中细腻的爱,让我懂得了人世间点滴的美好。而那个曾被外婆强迫留长发的小孩,再也无悔她这一生最宝贵的收藏——暖暖的记忆,深深的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