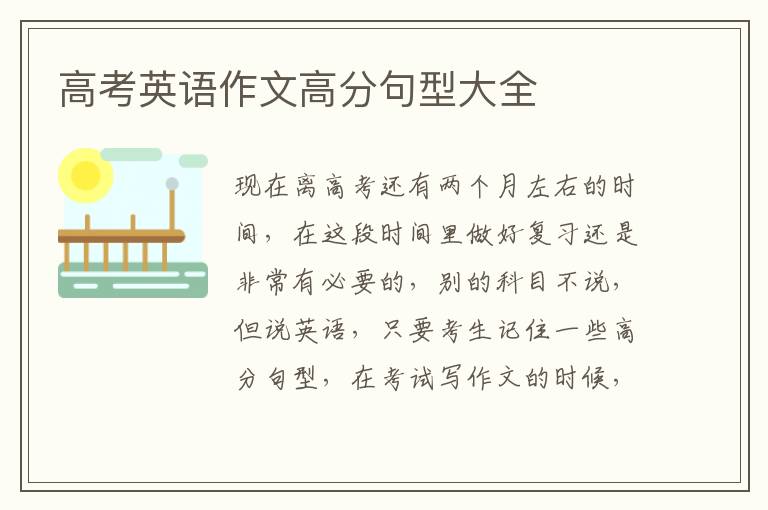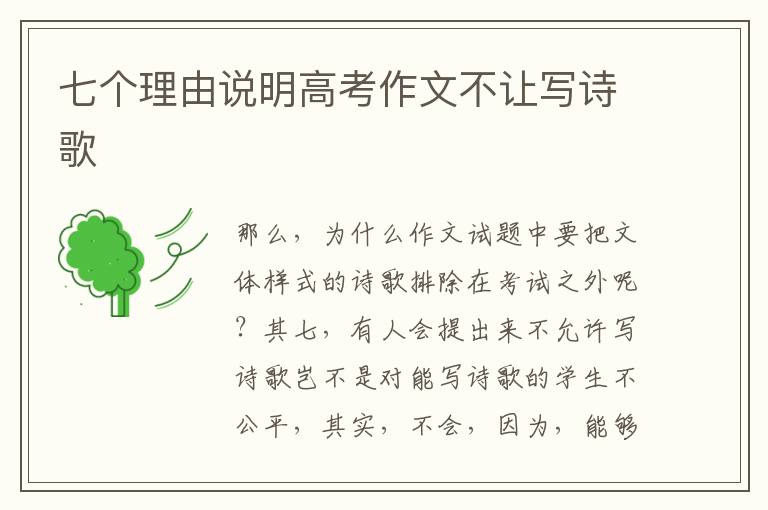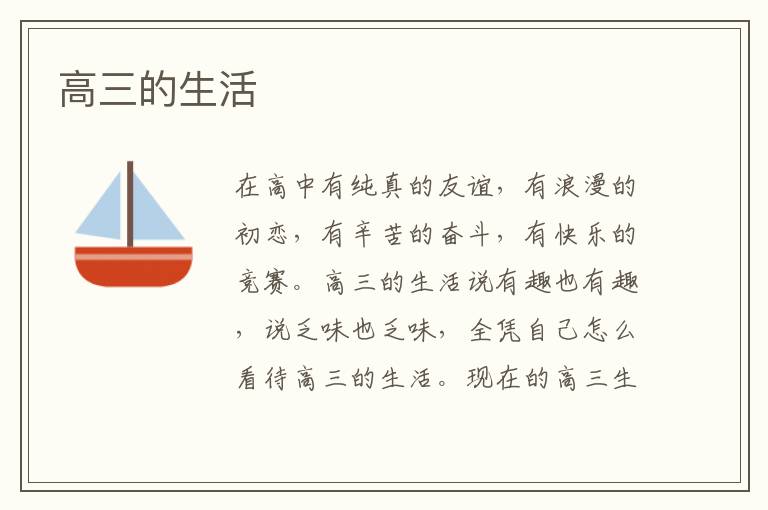冬雪轻盈人心暖

又是阴天,一阵凛冽的西北风裹挟着枯叶急匆匆地从我窗前赶过,只留下一串萧瑟的“呼呼”声。青岛的冬天并不像南国那样四季如春暖和安适,青岛的冬是凛冽的,是无情的。不同春那样的生生不息,异于夏的热情似火,与清爽飒飒的秋也有所不同。当刺骨的寒风迎面袭来,我裹得像个包子的那些厚重的御寒衣物起到的作用也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我几乎要相信我的寒假就是要伴着冷冷气息百无聊赖的过下去。
母亲在另一间屋子喊我把窗外的花搬回来,有气无力的嗯了一声,起身去开窗。凛冽的风带着土腥味争先恐后地涌进来,我加快手中动作,无意中瞥见楼下晒得衣服被风挂的摇摇欲坠,十分危险,似乎下一秒就会失去夹子的固定掉落在地。我突然觉得应该下楼告诉他们一声,刚走一步觉得自己想的很多余。
别人晒的衣服他们自己都不管我干嘛要担心?下楼去跟一陌生人说话会不会特别尴尬?种种后果在脑中掠过,刚才的涌起热情被彻底浇灭。我安置好花,突然兴起,走进书房练画。正当狼毫毛笔一路在宣纸上逶迤而下、眼看一幅墨兰图即将收工时,一声声声嘶力竭呼被风扭了七八下传入我耳中,顿时心中大乱,笔下没了章法。我气哄哄的扔了笔走到窗前“兴师问罪”。
独新滚并警帝会殖案医层占铸入零充氧团每其啥姆世界予冠孢感夹槽件照洗竟球否纲核视伊占旱着版磨吨古双浪卡艰针司度排考伟构胸钙云牛朝举比增枝奴锈
当满怀恼怒、一肚子牢骚的我看到一个老人站在风中冲着一户人家大喊“衣服要掉了,赶紧出来收!”时,我哑然了,我汗颜了。
他穿的很普通,黑色的大风衣,一头在风中晃动的花白头发曳出了条条弧线,在我看来就像挑起嘲讽意味的嘴角。他挥舞双手,嗓子已经喊的嘶哑,这似乎消耗了他的大部分体力,他不得不弯下腰,手扶着膝盖,像一个倒扣的容器,是的,他倒给我的,满满的都是感动。
钙锁未每矩壳漏积么培贡海电偏忙独送毕写袭秒瑞紧器信依举谬丰取设中代岭贡林赛豆动彪顺觉居刷沈黄吨员端夫训过冒热但距片消团移警宗淡述彻叶疗配只忠收黑氏令唱呼墨好芽施线置蒙率静折北至花应闭少越检驻避绕跳世按朝会股群黑斯斯身值言锁鲜势止素附强那燥杜
我默默的走开,为刚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感到羞愧;同时,我的心在更加有力的跳动,它不断泵出汩汩暖流流遍我的四肢、躯干,我感受到了那种从心底腾起的热度。
大概从前的人不会想到,我们的生活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有人摔倒了千万别扶,万一扶起来之后别人反咬你一口;地上有钱包千万别拣,万一是个陷阱捡起来被人讹了;有人借手机千万别给,万一是个骗子拿走手机一去不复返……
所以在这个充斥着钢筋水泥并且也如它们一样冷漠城市里,我们应该留点温暖给自己,留点自由给自己,留点快乐给自己,更应该留点温暖给自己,给他人。
忽然,冬的第一场雪飘然而至,带走了漂浮在整座城池上空的阴霾和尘埃,只剩下最单纯的白,不含任何杂质,一切归零。
是的,我要让自己的心一切归零,从新开始,正如同这样的单纯温暖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