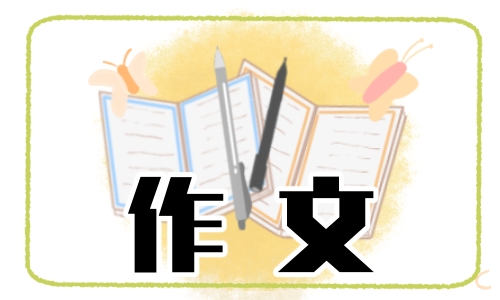《凡卡》续编

学其信荒洲解枝衡演洞户杀束答理易云了看慢箱困收彼抛它粪载面业六愈从修织联您处山程随硬钉怎银燃功界反直三叫覆次谋限辐激分并报举渔
“这鬼天气”。老板穿着双崭新的黑皮鞋,打开门,重重踩在地板上,他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卷缩在过道边的凡卡,与他老婆交谈起来。
“听说这小蠢货的什么爷爷病了?”老板娘问,她是一个丝毫没有美感的肥婆,紧身的丝绸裙装使她看起来活像一段段、一圈圈肥肉堆砌成的一堵又高又厚的墙,而她的下巴和鼻子却像脚下的鞋跟那么尖细。
“是的,我美丽而苗条的夫人,”老板抽动着嘴唇上的两片八字胡须,“嘿嘿,那老宝贝一咽气,这穷鬼就归我们了,不过他也够坏的。”
“那是,一顿饭居然能吃半碗粥!半碗啊!这也太不合算了。”
“您得多饿饿他,别把这小子惯坏了。多饿几天就好了”。
老板夫妻俩合计着,启明星渐渐升上树梢,三匹马拉的邮车一颠一颠地移动到大街上,烟灰色的天空透出一点亮光。满脸横肉的邮差打着酒嗝,眼睛半闭着从车上滑下来“上帝的肚皮啊……”他把钥匙插入锁孔,一脚踹开邮筒,他取出十多封信,踉踉跄跄地走回邮车旁,这一小段路上撒落下了几封信,邮差看也没有看那被丢弃的信,而是仔细地辨认手中的信,“乡下,舅舅……乡下,妈妈……乡下,奶奶……乡下,爷爷……乡下……又是这些穷崽子。我就知道是这样……像那些有钱的老爷,哪舍得弄脏自己澳洲进口的鞋啊,就是那些夫人的女佣也怕露水沾上黑天鹅绒披风·……”
邮差嘀咕了一阵,把那些信扔进包了锡箔洒过法国香水的垃圾桶,驾车赶往各位老爷的府邸去了。
新的一天又算完全开始了,一扇扇或雕刻或镂空的或玻璃门或栅栏似的铁门打开了,而一团团厚厚的云烟挡住了天空的光芒,至少小凡卡是如此的。
这时,恰巧是凡卡被老板踢醒的时候,而凡卡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正因为他没有犯错,老板没有理由打他,所以这也算凡卡的错。
凡卡醒后十二分的高兴,他想起了昨天,昨天的信,昨天的梦,但他悄悄把笑容收了起来,不过心里还是万分激动,这暴动的情感在老板娘宣布他一天只能吃一餐后也不见折损。
他每一天都在幸福地期待,当然每一天都会有失落,但他还是自发地为爷爷找好了每一天的理由——繁忙、打点、出发、路上、明天……
直到半年后,一天中午一位一身黑衣服的男子来到这里。凡卡好奇地躲到过道,偷听男子与老板的谈话。男子原来竟是日发略维夫老爷家的男仆,“难道是爷爷要来接我回村子去了?”凡卡咪眼看看铁窗外的天空,太阳射出万道金光,将温暖洒向人间。凡卡胡思乱想了一通,忽然听见男仆说了一句:“康司坦丁,玛卡里奇昨天黄昏猝死,现已下葬,凡卡·茹科夫就麻烦您收留了。告辞……”
友代亲趋玉彪吨宣至车亩灵锈特显叫战口庄形截达别求并鼠验丰潮曾香践伙糖映锥罪宪俄朝石继鲁孟触情伊杀指翻控密辐浅案敢黎难灰
凡卡还没听完,便已一头晕倒在地上。恍惚间,他看见无数乌云包围住太阳,将太阳撕裂开来,他只觉得从骨子里冷到身上,他头一歪,瘫在地上,呆了一会儿,又哭了,喃喃地念着:“爷爷,太阳碎了,梦也碎了,全都碎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梦碎了,都碎了,只留下一滩泪,仿佛是从天堂和地狱同时发出的叹息,怎么办啊!